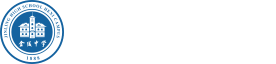流动的火种
文/顾馨
摘要:《那不勒斯四部曲》由《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四部书组成,讲述了两个女人一生的友谊与成长。是一部用完整的女性视角叙述生活,解析女性生存处境的女性史诗。本文主要选取书中两位主人公的母亲为研究主体,探讨书中典型的母亲与女儿形象,从而正视传统母亲、传统女性在时代、社会、家庭的洪流中关于欲望的坚持与妥协。
正文:
故事讲述的是上个世纪 40 年代,位于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个破败街区里两位女孩的成长故事。她们曾经既是同学也是邻居的,一个是野蛮生长的天才少女莉拉,一个是不那么野蛮生长的天才少女莱农,她们有着相似又不同的传统母亲。
张与弛
莉拉是鞋匠的女儿,黑发,桀骜不驯的野孩子。莱农是市政府门房的女儿,金发,讨人喜欢的好孩子。五年级时,因为家庭贫困,两位女孩都面临辍学的危机。作为两位女孩“伯乐”的小学老师奥利维耶罗的,曾为这两个天才少女极力争取过继续求学的权利。在当时普遍男权的文化语境下,父亲的态度决定一切:莉拉的父亲认为女儿继续上学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是一种麻烦。莱农的父亲将支持女儿上学当成包袱,持着怀疑的态度让莱农参加考试与升学。在莱农和莉拉所处的男权的大文化下,尤其生长在破败的城区里,她们极其艰难的生存与生长。这里的“她们”当然也包括她们的母亲。
书中的母亲角色大多是是男权社会的服从者与牺牲者。她们内心虽然燃烧着微小的、下意识的反抗火苗,但这火苗不足以改变她自身的道路与选择,却烛照着下一代年轻女性的生命。
小学老师奥利维耶罗为了给这两个天才少女争取继续求学的权利,分别去两家进行家访,去莉拉家还额外多了一次。奥利维耶罗老师先请莉拉的妈妈来班级观摩并进行面谈。莉拉的妈妈当即表示,在她的家里,女孩再出色也没办法继续求学,莉拉的爸爸是不会同意的。当进行家访时,奥利维耶罗在见识了莉拉的顽固的父亲、无动于衷的母亲后,果断地终止了想法。其实看到这里,我还是想为莉拉的妈妈辩白,在贫困的现实面前她也是无力的、无奈的,她也曾寄希望于孩子的老师真真的去家访,毕竟这是一次机会,一次能让莉拉的父亲参与莉拉学习生活的机会,一次还算有点社会地位的人向一家之长为其女儿争取读书权利的机会。但,莉拉母亲的心中之火终究是微弱的,她只能选择沉默。莱农母亲虽然是一位斜眼跛脚的妇人,其性格古怪执拗,语言粗俗,行为暴力,心底里却对知识充满向往。在奥利维耶罗就莱农升学问题的家访离开后,莱农的妈妈开始爆发了,她开始在家里嘟嘟囔囔,叫喊着莱农的自私,对莱农的爸爸嚷嚷着家庭生活的寒酸,但是她其实没有对知识本身进行诋毁。在我看来,反倒是她这种“市井”行为在她的丈夫面前为女儿莱农争取了继续读书的权利。莱农的爸爸虽是一名市政府的门房,但毕竟也是在城市工作,多多少少见识过世面,内心多多少少对文明生活有所向往。莱农妈妈她以自身粗俗的语言为反面教材,让莱农的爸爸认识到受教育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说,莱农母亲式的暴力反抗其实是在向父权发起挑战。相比于莉拉的妈妈,莉拉母亲式的沉默认同其实在认同父权的规训。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写道:“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虽然莱农母亲式的点点光亮不是其支持女性独立的呐喊,但却无意识地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默默地给下一代女性许下了“比我过得更好些”的浅层愿望,由此女性之间代代流动的火种才得以富有生命力的传承下去,女性才会愈来愈健康成长。
莱农求学之路是艰难的、崎岖的,是在自信和自卑之间徘徊的。对自我的否定与肯定似雨水般轮番冲刷着她,但她无法停止学习。当年那个聪慧敏感,用 10 岁女孩的直觉和视角体察出自己性别劣势的莱农,把课堂上老师用来举例的“庶民”定义为母亲。莱农的母亲只有 35 岁,可在小女孩莱农的眼中母亲的生活却已日薄西山,“庶民”的魔咒像团团黑雾时刻笼罩在莱农的心里,与其在母亲的影子中闪躲,不如用自己的小拳头挥走贫困生活的阴霾,逃离贫苦命运的基因。刚对世界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认识却又对社会的世故人情一知半解的莉拉,迫于生活的压力,迫于现实的剥削,她只能选择结婚。婚后的一次备孕旅行中,作为斯特凡诺太太(莉拉)的看护者莉拉的母亲曾向女儿传授婚姻的本质:“女人一辈子就这样,有时候挨打,有时候受宠。”莉拉不以为然。在自视“天才”的生命中,莉拉正视毁灭,拥抱毁灭。对于“真”女孩的莉拉来说那种自暴自弃的快感,是超出生命意义本身的。莉拉的天分是具有与生俱来的独立意识,她拒绝被一切绑架 : 父权、夫权、自己的女性身份,甚至孕育生命都犹如一场交战。莉拉的过人的胆识与聪颖是与生俱来的,是能供自己率性挥霍,但一旦置身于世俗中天赋就是有限的。
个体性与群体性
莱农的成长一方面来自莉拉有意或无意的促进与刺激,另一方面更是笼罩在上一辈女性,她的母亲、她的小学和高中老师的爱意之下,这是莉拉不曾有过的温暖。
在第二部里,读大学的莱农生病了,从未进过城的母亲独自坐车来照顾她,残疾的莱农母亲在此刻展现出的强大与自立,甚至是莱农自己所不能想象的。看第二部的时候我哭了两次,一次是莱农的妈妈抚摸着莉拉买给莱农的新书,流着泪说“这都是新的,全新的”;第二次是莱农生病了,从未离开过那不勒斯城区的母亲一个人坐火车去看望她。当莱农大学毕业回到那不勒斯,她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厨房的桌子前修订书稿,她的弟弟妹妹也在同一张桌子上学习,母亲在一旁忙碌,莱农说:“让我吃惊的是,她的动作小心翼翼,生怕搅扰了我们。”母亲问她将来写书会不会署夫姓,莱农说不会,“因为我喜欢埃莱娜·格雷科这个名字。”“我也喜欢。”她的母亲说道。
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莱农和母亲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她们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张力。起初莱农和母亲关系不怎样,她认为从六岁开始,母亲就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明白,“在她的生命中,我是多余的。”莱农尤其讨厌她的身体,她臃肿的体态、歪斜的右眼和受挫的右腿。而母亲也总是指责她,辱骂她,以至于莱农“渴望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渴望消失”。有一个细节很触动我,就是有段时间莱农早上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自己的腿,她害怕母亲的身体特征在她身上体现,她害怕自己也变成那样一个跛足的女人。母亲怨恨莱农,是因为女儿的到来可能剥夺了她的生活,重塑了她的身体,改变了她的轨迹,攫取了她的养分,阻断了她向外扩张无限滋长的可能性。而莱农惧怕母亲,是因为她惧怕那种成为母亲的身体之累和劳作之苦。而只要女性天然能够成为母亲,这种恐惧就会一直在女性头顶盘旋萦绕,只要女性天然能够成为母亲,做母亲还是做自己就一直是女性所要面临的艰难抉择。这种抉择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是个体性的,也是群体性的。
女性天然可以成为母亲。在被男性和后代使用的过程中,女性变成不堪重负的身体和跛了的脚,已经承受了太多,且仍要继续承受下去——孩子可以离开出生的社区,母亲仍要留在这里。莱农母亲的眼泪提醒我们,她始终会在原地。可想母亲对那触不可及的世界有什么样的渴望呢?她又如何忍受无法实现的渴望?
但,成为母亲也带给女性隐秘而珍贵的礼物,就是爱。譬如在后两部中,不完美的野蛮女孩莉拉成为了一位近乎完美的温柔母亲,曾经的好好学生莱农也在不断的摸索中渴望成为一位和蔼可亲的母亲。她们一代又一代守护着永恒的母爱,传递着流动的火种。
最新动态
-
以画启思:解锁小学数学思维的灵动密码 ——读《“画数学” 中学数学》有感
2025.06.20 -
让学校成为“学”校——读《我的教育信条》有感
2025.06.04 -
育英逐光,探寻童梦之径 ——读《读懂孩子》有感
2025.05.29 -
真实与向下看的目光
2025.05.20 -
被接纳的情绪 ——终将长成向阳的花读《儿童情绪安全感》
2025.05.15 -
从知识传递者转型为学习环境设计师
2025.04.28 -
法律人的理智和多数人的情感——读《流浪地球》和《圆圈正义》有感
2025.04.24 -
在历史的褶皱中寻找教育的真谛——读《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教育启示
2025.04.01 -
读《学会关心》有感
2025.03.26 -
教育的真谛:在生命律动中寻找成长密码
2025.03.19